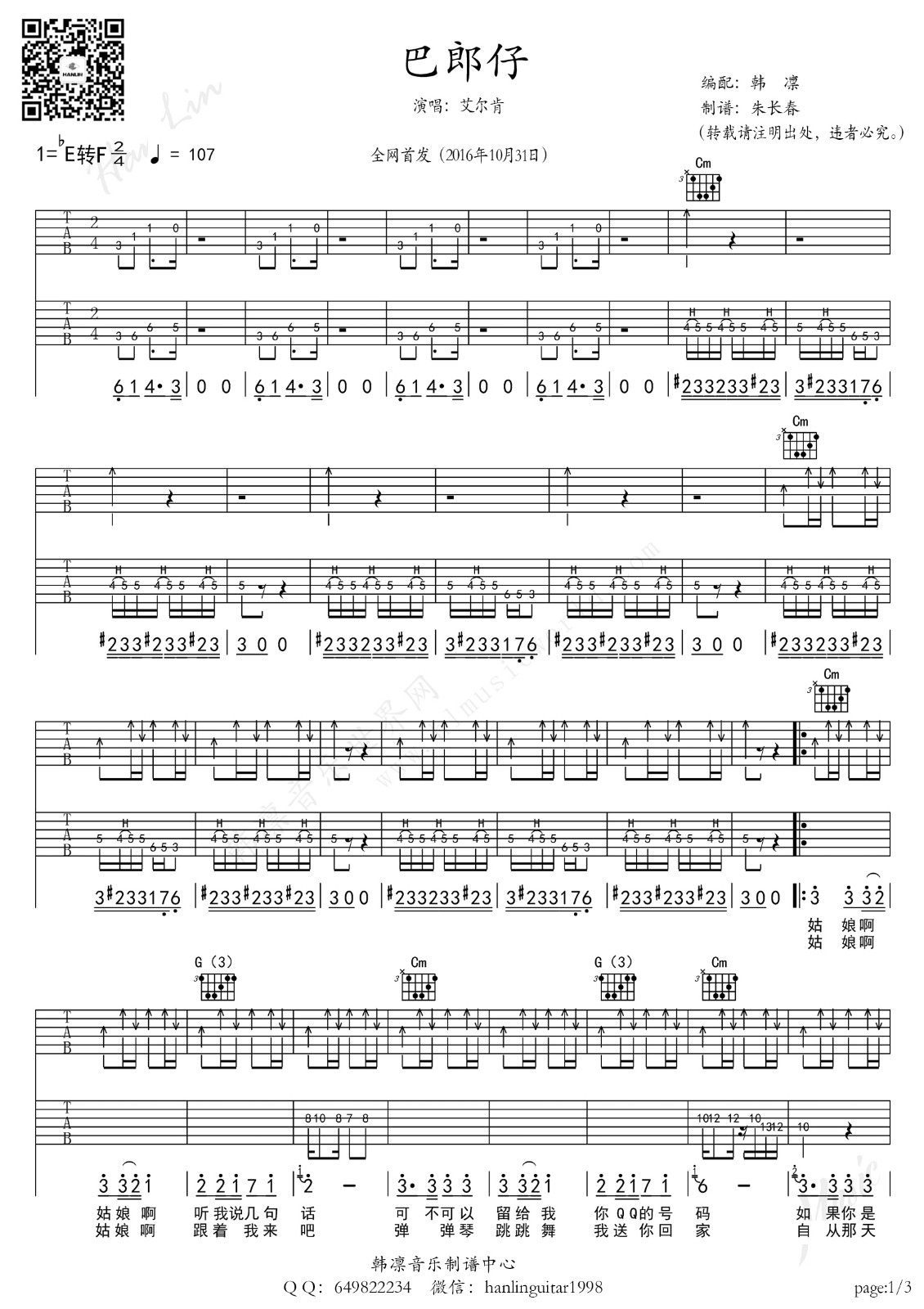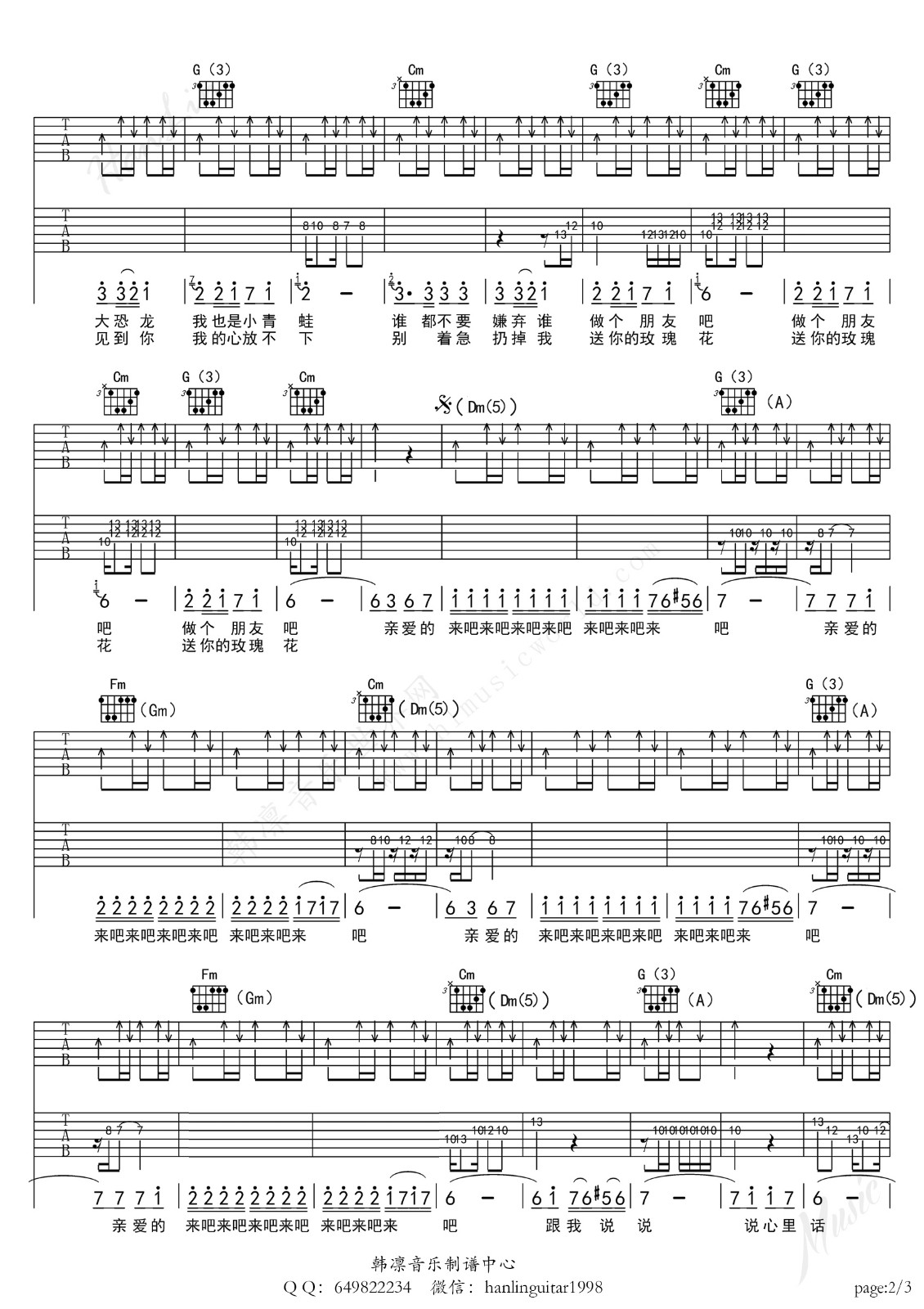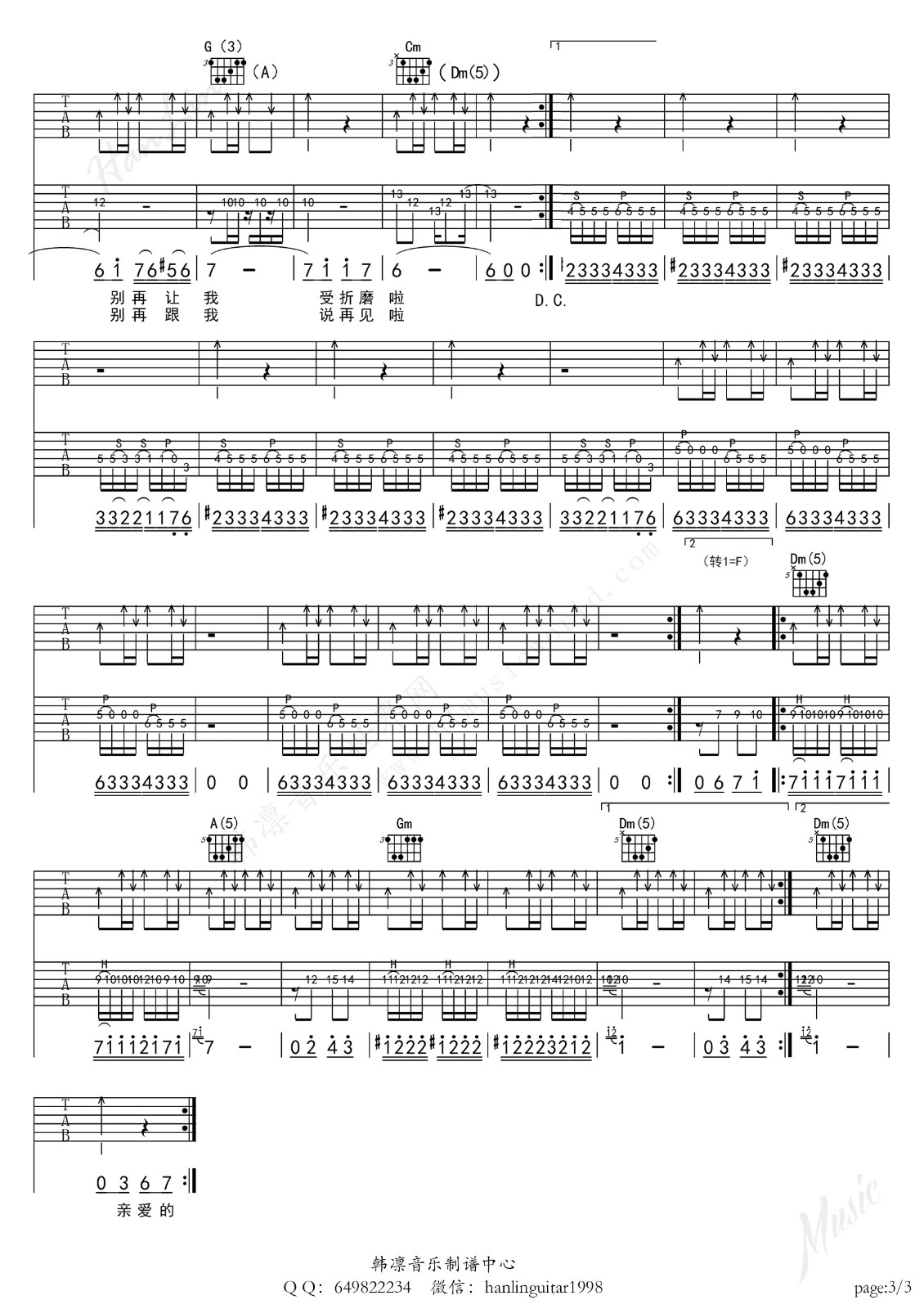《巴郎仔》以质朴的歌词勾勒出边疆少年的生活图景,通过白描式意象传递出坚韧与希望并存的生存哲学。戈壁滩上的脚印与胡杨树形成时空对话,沙枣花与驼铃声在粗粝环境中绽放出生命的柔软,构成刚柔并济的审美张力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走"字动词链,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轨迹,也隐喻着代际传承的精神跋涉,月光下打磨腰刀的场景将实用技艺升华为精神仪式。干旱土地里长出的歌谣具有文化人类学意味,沙暴中护住馕饼的细节揭示生存智慧与食物敬畏,皮匠父亲佝偻的剪影投射出手工时代的最后微光。作品巧妙运用边疆风物作为情感载体,坎土曼的锈迹与卫星天线的反光形成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位,未完成的木雕小马保留着手工时代的温度。全篇通过物质性意象群构建精神坐标系,在60个字的标题限制中完成对边疆少年成长史诗的微型叙事,让戈壁风沙与青春血性在词句中碰撞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咏叹。